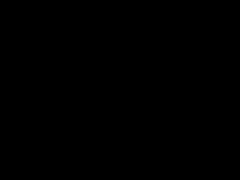|
在云南会泽县大井镇的山坳里,一栋闲置的乡村建筑墙体斑驳,玻璃蒙尘。这里曾是会泽县大井镇卫生院黄梨树分院的旧址,也是宁佰万一家二十年悲欢的见证。从响应公权力号召举债建所,到机构几度变更性质,再到撤销与复议的反复拉锯,这场围绕乡村卫生机构的行政纠纷,暴露出基层执法与监督体系中的深层矛盾。
公权力主导下的“建所—变更—撤销”三部曲 时间回到2002年,会泽县卫生局、大井乡政府等部门联合发文,将宁佰万从马安村委会调配至黄梨树村委会,要求其投资建设村卫生所。这份带有行政指令性质的《组建实施方案》,让当时还是乡村医生的宁佰万坚信这是“为国家做事”。他东拼西凑举债建起房屋,成为黄梨村卫生所负责人。 2003年,因原村医不愿合并,经三级部门同意,卫生所改设为“大井镇卫生院第一门诊部”;2006年,又升格为“会泽县大井镇卫生院黄梨树分院”,明确为全民所有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。会泽县卫生局为其核发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,注明宁佰万为负责人,同时赋予新农合报销权限,指定镇卫生院派驻医护人员——这一系列具体行政行为,为分院的合法性奠定了制度基础。 转折发生在2008年5月16日。会泽县卫生局突然发文撤销黄梨树分院,援引《执业医师法》和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相关条款作为依据。但这份撤销决定,随后被县政府2009年的行政复议推翻。复议决定书明确指出,撤销决定“证据不足、事实不清、适用法律错误、程序违法”,属无效行政行为。
生效文书成“沉睡条款”:五年空窗期的民生代价 按照法律规定,2009年5月13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,本应成为纠正错误的终点。会泽县卫生局甚至书面承诺,若2009年5月28日前未起诉,将履行复议决定。然而,这个期限成了宁佰万维权路上的“分水岭”——此后五年,复议决定始终停留在纸面上。 “卫生局既不起诉,也不执行,就这么拖着。”宁佰万回忆,分院药品过期变质,医疗设备锈蚀报废,他举债建设的房屋闲置至今。更致命的是,他的乡村医生资格被恶意注销,失去了谋生手段。一家人陷入“孩子学费靠借,日常生计无着”的困境,“最困难时,锅里连米都没有”。 2013年底,在宁佰万跪求县领导后,大井镇卫生院才按半价收购了过期药品和部分设备,核销了部分新农合补偿款。但截至目前,仍有70354.7元补偿款被镇卫生院拖欠,这笔钱是当年分院为患者垫付的报销费用。
三级监督体系为何“层层空转”? 一份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,为何能被搁置五年?梳理整个事件,监督体系的缺位尤为刺眼。 会泽县政府作为复议机关,在撤销原撤销决定后,未履行法定监督职责,既未督促卫健部门恢复分院运营,也未组织和解,被指“监督不力、行政不作为”。而省、市两级部门在接到申诉后,仅作转办处理,未采取责令整改、约谈责任人等实质性措施,形成“层层转办、层层空转”的怪圈。 更值得关注的是,会泽县卫健局在复议决定生效后,采取了一系列“变相阻挠”措施:不派医生、停新农合报销、刁难许可证校验,甚至注销申请人从业资格。这种“以权压法”的行为,使得行政复议维护合法权益的立法初衷落空。 2014年,宁佰万向省政府提起行政申诉,省、市两级均要求会泽县依法处理,但问题仍未解决。直到2025年5月,上级第六巡视组将此案转交省司法厅,明确要求一个月内办结,这起沉寂多年的纠纷才重现转机。 乡村治理中的法治考题:谁来为“程序空转”负责? 在黄梨树分院纠纷中,几个关键问题值得深思:当行政机关拒不执行生效复议决定时,监督机制应如何发力?公权力引导私人投资后,如何避免“卸责式”执法?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所研究员指出,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,复议机关对生效决定的执行负有监督职责,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履职情况也有监督义务。“会泽县的案例中,三级监督体系同时缺位,反映出基层法治建设中‘重决定、轻执行’的倾向。” 更值得警惕的是,会泽县卫健局将责任推给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的大井镇卫生院,试图以“民事纠纷”掩盖行政责任。而2013年的半价收购协议,被宁佰万认为是“以民事行为替代行政赔偿”的无奈之举——“卫生院没有行政许可权,凭什么处理卫生局批办的机构?” 如今,上级巡视组的督办让这起纠纷迎来新的可能性。但对宁佰万而言,二十年的维权路早已超越个案本身。“我要的不只是一笔补偿,而是想弄明白:为什么生效的法律文书,在基层就落不了地?” 在乡村振兴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双重背景下,黄梨树分院的命运,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的生计,更考验着基层治理体系将“纸面上的法‘转化为’行动中的法”的能力。这场跨越二十年的纠纷,终将成为观察中国基层法治进程的一个微观样本。对此,媒体将针对此事件持续跟进报道。 来源:晨报资讯
|